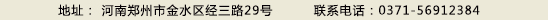我曾住在花市东三条
我住的东三条是老百姓的叫法,在地图上你找不到它。官称是“下下三条”,但你要理所当然地去下下三条找,你还就真找不到。它没按长理出牌地夹在了下下二条末尾与下下三条末尾之间,胡同的东半截没有门户,西半截只有4个门牌,可能是老北京数得着的住户最少的胡同之一了吧,它隶属东花市派出所管辖。
出崇文门往南路东,在护城河的南岸与花市大街之间有一大片住宅。这片住宅被四条自崇外大街起至白桥大街止的东西向的胡同分隔,分别是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又被北南向的羊市口、小市口、虎背口三条胡同拦腰截断,自西向东地分为上×条、中×条、下×条、下下×条。是非常标准的棋盘街,正南正北的方位,笔管条直的三里多长的胡同。
顺虎背口胡同北望,正是内城的东南箭楼,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下下三条的大概方位了吧,在东便门的南面。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爬蟠桃宫门前的石狮子,骑大石桥的汉白玉栏板,在桥下河水哗哗的冲击声中,看叽叽的雨燕在箭楼周围穿梭飞掠。
在下下三条往东约三分之二处,有条南至下下四条北至下下二条的南北小胡同,将下下二条与下下三条、下下三条与下下四条之间的住房又拦腰一截,可能是它不同于羊市口、小市口胡同那样贯穿头条与四条,所以小胡同没名。
南边的小胡同中间西侧有一住户,靠三条把口是座水井房,大家从这井里挑水吃,也有专门送水的。在木轮的板车上放一像现在高腰木澡盆一样的大木椭圆水桶,上面是封闭的,留有一方口,从上灌水用,将水桶灌满后,用一木盖儿盖上。在靠车后面的木桶最下方有一圆孔,用木塞子塞住,送水人将车拉到用水的住户门口,放好水筲,拔下塞子,往水筲里装水,放完水再用木塞子塞住,而后把水给人家挑进院子,再倒进人家的水缸完事。买水的人,有临时现叫的,也有买票的,买票的有没有优惠就不知道了。不曾想这行当在断了几十年后,居然还有了发展,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了,送的水也是五花八门了。
北边的小胡同就不一样了,在小胡同西侧靠下下三条这边有一开门,是于姓家。进门是一空场,空场靠北中间部位又开一门,那才是通往住房的门,空场靠西南一隅是棵百年老槐树,要两人才能合围起来。
小胡同靠东边一侧中间部分是条向东的胡同,等于是并行下下二条与下下三条的胡同,这胡同是这么大一片住宅区中的特例,绝无仅有的。这胡同靠西头这边依次南北错位对着开有四个门,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喜庆中,我就出生在南面第二个门里,下下三条22号(可能号码不正确),是正宗的共和国同龄人。
这是一个最普通最简约的小四合院,北房四间,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是两间,院门开在西北角。这边房屋都是私房,是一姓相的房产主的。
我家住北房中间的两间和东西厢房各一间,相对来说比较宽裕。父母住北房的里间,老弟弟也出生在这儿。那时都是医生来家接生,我还问父母,小弟弟是从哪来的,他们告诉我是医生把小弟弟放在那医药箱里带来的,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答案了吧?我和两哥哥住外间。东厢房是爷爷奶奶和大弟弟住,西厢房则是厨房兼杂物间,有时老家来人也住在那里。
这种房子间量都比较小,估计也就在8㎡,而且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通常室内是不烧火取暖的,一是没有地方放炉子,二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经济上的不富裕吧。那时没有针织衣物,都是光板穿棉衣,条件好点儿的,才能穿得起棉布小褂和高筒袜。为小孩能愿意起床,父母往往要先在厨房火炉上把棉袄、棉裤用火烘暖和了,再给我们穿。在寒冬腊月天,滴水成冰,爷爷奶奶的屋通常还是要生上一小炕炉火,烧烧炕的。现在是见不到了,那炕炉是城市住房的特殊产物,实际就是微型的带四个脚轮的小火炉子。小炉子也就有现在的10升的桶大小,烧一炉煤球(那时没有机制型煤,要不是请人家摇,要不就是自己攥一些),坑洞很浅,只能放一小炕炉,不像农村那种烧柴火的炕,炕洞很深,可以加很多柴火,所以炕烧得只是温和而已。
北房西间壁儿是孙家,一家四口,一老太一小孩,加两大人,老太太特别爱用支炉烙饼吃。孙先生则是好吃炸酱面,左手托一大海碗,那面上一摊炸酱几瓣蒜,右手是一条黄瓜。用酱拌上一点儿面,吃上一口面,咬一口蒜,再吃口黄瓜。然后是再拌上一点儿面,再吃口面就口蒜,再吃口黄瓜。让人看着就透着那么香。
东间壁儿是苏姓老太太,有一儿子是拉洋车的,不经常来,来时就把洋车放在他们老太太家与我家东厢房的夹道那儿,我特别纳闷,那车是怎么进院的呢?要知道,我们院门口可是有两步台阶的呢!老太太经常让我给到虎背口她买油盐酱醋啥的,每次都给一二分的小费,受利益驱使,我是乐此不疲。几乎是每天晚上在炉火将熄灭时,老太太都会把一个窝头放进炉膛里,第二天一吃焦酥焦酥的,特别香,比那种切片炕的香多了。虽记忆犹新,但无法效法,几十年了,终没有了这口福。
东厢房那一间住的是盲人夫妇,带一小孩,大家给他们帮不少忙。小孩特别白,也特别好看,只是太小,我没抱过他。他们平时也点灯,有好事者问他们,你们点灯也看不见,不是白费电嘛?由此我知道了歇后语“瞎子点灯白费蜡”在这儿的隐晦。
南房住了四户,两边两户记不清了。中间东边那户户主叫朱明远,是北京车辆段的检车工。夫人个头不高,很精明,我叫她四姑,不知是怎么论的。他家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年初中毕业后去了三线,在金沙江那边,去一趟单程要走上小10天呢。老二叫朱全有(后改名叫朱清有),是我小学同校同学、中学同班同学。老三叫朱全来,老四叫啥记不清了。记清的就是四姑蒸的小刺猬,绿豆做的眼睛,刺毛是用剪刀密密地剪出来的,特别形象,让我好喜欢。他家孩子多,也就占了西厢房的另外一间。
中间西边是我五姑结婚住在那。我五姑是色织厂的工人,她们结婚时没在院里办,可能兴新式的,在厂里由工会给操办吧。只记得是满屋子的镜子,各式各样的,摆在桌上,挂在墙上,平面的,磨花的,都写上了贺词。
那时没有什么玩具,小伙伴们经常玩儿的是捉迷藏。不管是躲在昏暗的灯影里还是藏身某一院门的后面,前后几个胡同都是匿身之地,总要玩个不亦乐乎,直到家长们大呼小叫地给招呼回去为止。
还有一件隐私。小胡同里没男厕所,大人只能到蟠桃宫后身那儿(下下二条东口)。我们院的东边、两房之间有一露天的简易女旱厕,我使用过,还让人家逗笑过,真不好意思。
我爷爷在车辆段上班,父亲在霞公府(现址是北京饭店)那儿上班,是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我们算是铁路家属,因此,我大哥先在铁六小上学,后转到铁一小,可能是父亲上班好顺路带他吧。我和二哥都是铁六小的,我们上学要么就顺胡同向东走,要么就绕道虎背口,在虎背口南口那吃早点。
虎背口南口是一大下坡,坡度大,往里走是骑不了车的,只能推行。把口路东是一粮店,粮店与大马路落差大,是用一个个磨盘当挡墙的。小吃摊就设在这磨盘前。当时最爱吃的是面茶和炸糕,特别是炸糕,人家事先已包好,用湿布苫着。一坨坨的排在一起,像牛粪似的(现在牛粪是一滩滩的)。
吃完早点,然后再顺东花市东大街去上学,这条大街叫什么一直没闹清,只知道西头叫“铁辘轳把”。东花市大街在此分岔,一条斜街通向广渠门,因路过一卧佛寺,故叫卧佛寺大街。文革时改叫东花市斜街。
我们上学走到白桥大街,路东是片菜地,沿菜地南边的土路直到京山铁路路基下,再顺路基旁的一条窄窄的北向南的斜坡道走到简易的雷震口道口,通过道口再往北走一小段,基本到道口房前,有一大下坡直通南北雷震口分界处的大槐树那儿。由于坡度大,只能走自行车。我们淘气,有时就一路奔跑而下,蹚起阵阵尘土,一不小心有时趔趄,有时还要摔个大前趴虎。有时也要故意不着急走,特别是下学后,常常要等火车经过,体会那山摇地动和蒸汽笼罩的感觉。还特别爱看火车司机伸出手臂去接铁路路票的情景,幻想着哪一天也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铁六小在南北雷震口中间,那里基本上都是铁路宿舍,一排排的红砖房,与东外城墙一路之隔(放学后爬城墙是当时一项主要娱乐项目)。南雷震口宿舍的南边和西边那会儿还是菜地,南面是一条东西向的沙石路,从护城河逐步抬高至铁路路基,然后是大下坡直到原女十五中前。西边菜地分两截,一截与铁路路基齐肩平,可能是修铁路遗留下的吧,也让人种上菜了。一畦畦的,靠广渠路那边还有一马拉的提水车。巨大的平置铁轮用拨齿拨动垂直铁轮,带动提斗往而复始地往上提水,浇灌菜地。还有些为数不多的阳畦,就是在畦的北面用土坯建一道矮墙,然后搭上大竹片,那头弯到地上。间隔不大,晚上用草帘子苫盖,白天敞开,种些韭黄、小菠菜什么的。与现在的塑料大棚相比,逊色多了。
这都是前半个世纪的事了,光阴何止似箭啊!那一片房子全拆了,雷震口也全拆了,连个念想的地都没有了。
阅读往期内容北京治疗白癜风的权威医院北京治疗白癜风的费用多少钱
转载请注明:http://www.js-zodiac.com/jhcp/73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