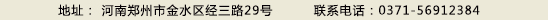专家观点蔡丹君中古文学中的田园饮食与
蔡丹君
乡村社会是生成中国文学的土壤,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基本环境。《诗经》中的田园诗,陶渊明躬耕南山的悠然之辞,唐人描写京畿近郊隐逸生活的诗文等等,说明乡里社会中基本的生活、生产场景,都曾是文学热衷反映的内容,而乡村风景甚至在关于“方之内外”的想象中被升华为一种生活境界,被文人赋予精神栖居的意义和价值。从社会意义上讲,乡村中的土地与人口、聚落与宗族、民户家庭、思想与信仰、民风民情、乃至乡村的控制与管理及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等等,都是关系到文人及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乡里社会的基本思想和民间宗教信仰,是文人的精神生活环境之所在。乡里宗族关系则是文人社群活动的重要依据。一言概之,乡里社会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土壤,又是文学乐于表现和反思的对象。马新说:“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点,也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源泉。打开中国历史,一幅是城市中国,一幅是乡村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汉唐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城市社会,城市只是政权、军事权和统治权的释放点,它统治着乡村社会,主宰着乡村社会,却无法改变乡村社会的本来。相反,中国古代的城市,恰恰是乡村社会的伴生物,是乡村社会的城市。”[1]可以说,中古时期,相比较于乡村而言,城市的存在反而是不够稳定的,在为文学发展提供基本环境的过程中,乡里社会的地位、功能和意义皆不可忽视。“乡愁”,如果想让它具体化,那么,除了那些家乡风物,最让人能联想起来的,莫非是故乡田园之间的饮食。这些内容在中古文学中已经有所透露,到宋代以后,更加蔚为大观。今天抛砖引玉,举几个例子,来强调田园饮食书写与情感记忆的之间关系。崔浩:乱离岁月中的饮食记忆
北魏崔浩曾是三朝重臣,地位显赫,对北朝文化的发展深有影响。他的家族,长期担任北魏第一谋臣。比如他的父亲崔玄伯,是汉族士人中最受北魏拓跋鲜卑皇帝信任的。他曾经建议道武帝改元、迁都,道武帝都照办。崔浩在太武帝时期,风头一度风头无两。但是,虽然在政治上足智多谋,《魏书》却说他“不长属文”,也就是说文学水平并不高,导致他现存的作品也的确数量不多,且大部分是与他政治地位相应的章奏符表、碑铭颂诔,难于从中看到他内心的细腻情感。在这些作品之外,好在还有一则类似短小散文的《食经叙》流传至今。它的片言数语,是崔浩对于乡里生活的回忆,饱含追忆往昔的真情,也反映了北方乡里宗族社会生活的一些真实场景,值得一观。《食经叙》是崔浩所撰《食经》的一篇序言。《崔氏食经》今已遗佚,而《食经叙》尚存在于《魏书》中。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著作被著录为《崔氏食经》四卷,与崔浩自己说的九篇之数有异,这可能内容有所遗失造成的。从《食经叙》的内容文字来看,《崔氏食经》的正文内容,应该是由崔浩的母亲卢氏口述,然后由崔浩整理而成的。作为崔氏族中的一名普通持家妇女,卢氏的生平故事,在史书中当然难见记录,而崔浩的《食经叙》则用寥寥几笔中塑造了一个勤俭聪慧的卢氏形象,无意使她留名至今。《食经叙》全文曰:余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温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聪辩强记,皆此类也。亲没之后,值国龙兴之会,平暴除乱,拓定四方。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梁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故序遗文,垂示来世。
崔浩所记,文字明白易晓,无需解释,他主要展现的是北朝乡里宗族生活中的一些场景。
在北方,妇女持家是寻常可见之事。“诸母诸姑”在大家族中共同参加劳动的生活场景,井然有序。崔浩对此耳濡目染,对家族中的妇女长辈们“温习酒食”的行为颇为尊重,称为“妇功”。崔浩也在其中回顾了家族经历的一段漫长的困难岁月。崔氏一族,在永嘉丧乱时没有随其他大族南渡,而是留在了政权更迭频繁、战争频仍的北方。而此时城市遭到极大破坏,胡族政权难于依附,所以像崔氏这样的大族,大多聚居于乡里,以避丧乱,至于饮食方面,是勉强糊口而已。面对生活的艰辛,北方的人们往往躬自劳作,且对于食物往往十分看重,生活极为节俭。在崔浩人生的头十余年间,他都难于看到恢复到过去排场的饮食、陈设。这种清俭的生活,其实也意味着北方的人们逐渐在新的历史时期迫于生活压力而放弃了过去的一些传统。崔浩的母亲卢氏,同样出身河北大族,她担忧过去的宗族饮食传统在日月消磨中被遗忘,于是嘱咐崔浩按照自己的口述,写下了简明易记的《食经》。崔浩在这段序言中最为动情的,是他所写到的自己在母亲去世之后的心情。崔浩在北魏龙兴之初,就地位显赫,一度是获得拓跋鲜卑统治者第一重用的汉族士人,所受赏赐丰富。而此时,为母亲的《食经》作序,他的思绪回到了平生之中的那段清俭岁月,并类比为“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可复得”。“季路负米”是一个春秋时的孝道故事。季路即子路,是鲁国人,因家庭贫困,自己常常野菜充饥,但不忍父母同样如此,遂去百里之外买米还家,供养双亲。负米之途,寒天暑热,无比艰辛,而子路并不懊悔和怨恨。待到子路在楚国为官,珍馐不断,父母却已经离世。即使想再去负米,也不再可能了。所以,崔浩这里的“不可复得”四字,是对母亲的思念和对过去生活的深深追忆。崔浩的文章,很少有像《食经叙》一样,充满对乡里生活的回忆,默默表达着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感动。这篇文字,语言平实朴素,娓娓道来,却触动人心。崔浩《食经叙》中提到母亲为家族的四时祭祀亲自劳作、百般省俭的场景,在当时北人的生活中是常见的。对于北人这些特点,由南入北的文人颜之推颇有感慨。《颜氏家训·治家篇》曾如此对比南北在俭奢问题上的区别,“生民之本,要当稼稽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树圈之所生。复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令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北土瘠薄,谋生艰难,不似南方水乡富饶,出产丰富。当时,北人节俭而南人奢侈,盖因后者之食物因其季候便利更为易得。《魏书》中所记载的弘农杨氏杨播家族,对待食物同样是谨恪。他们有一套家族饮食礼仪。首先是“不集不食”,就是说必须聚齐在一起方才开始饮食,共同分享然后是“每有四时嘉味,辄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杨氏的饮食礼仪,应该也是从“手自亲焉”的乡里生活中所得来。北方的妇女尤其需要在乡里生活中扮演重要的劳动角色。颜之推就发现,“河北妇人,织任组训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作为村居者的北朝乡里士人,在生活中崇尚俭朴、恪守礼法,这种生活记忆投影在他们此后的行为经历之中。《隋书》记载名臣房彦谦虽然“家有旧业,资产素殷”,且又有“前后居官,所得体禄”,但都散之宗族亲友,自己“家无余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北人还崇尚立身应该“会当有业”,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立身之本,即“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别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崔浩会将卢氏所承担的家庭责任称为“妇功”,正是看到了母亲及家族内的其他妇女在承担家庭角色时的尽职尽责。乡里社会的秩序感和社会责任的分工,让乡里士人秉持了务实的生活态度。长期经受战乱的人们,必须面对“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颜氏家训·勉学》)的现实。因此,北人躬自劳动,热衷事务,不废立身的品质。北魏名臣高允,政治地位曾经仅次于崔浩,但他与子女在进入到都城平城之后,居于草屋,府中饮食,惟有盐菜而已,子女“采樵自给”,保持了在河北时的生活方式。北人生活经验丰富,故而在文学作品中常注入了更多真切的心得,对日常生活的点滴有着充沛的感情。北朝晚期的乡里士人卢思道《劳生论》,在过去仅仅被解释为是抒发对社会不公的牢骚之论,但事实上它反映了北人在乡里的日常生活中较为真实和愉快的一面。这篇文章写于作者50岁时,目的是“追惟畴昔”,感叹自己“勤矣厥生”。文中这样谈到自己的躬耕生活:若乃羊肠、句注之道,据鞍振策,武落、鸡田之外,栉风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称弊,此之为役,盖其小小者耳……耕田凿井,晚息晨兴,候南山之朝云,揽北堂之明月。汜胜九谷之书,观其节制,崔寔四时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谈谷稼,沾体涂足之伦。浊酒盈樽,高歌满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乐也,子或以是羡余乎?
卢思道在躬耕生活中虽然备尝艰辛,但又享受这种“野人之乐”。“候朝云”“揽明月”“晨荷蓑笠”“夕谈谷稼”“浊酒盈樽,高歌满席”等句子,皆饱含诗意。而阅读农书,也是很有趣。在这种躬耕者所构成的乡里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一种价值取向,那就是追求真善美:“真人御宇,斫雕为朴,人知荣辱,时反邕熙。”这些对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关切,也正是北朝士人不同于深宫之中的南朝文人之处。北朝文人立足于乡里生活的“底层性”,正是他们之后能够拥有更为饱满之情感的主要原因。庾信:流寓者的异乡饮食
初到北周,处境孤独、经济贫困的庾信,将他最为真实的情感,放在了那些有精神栖息意味的田园诗中。这些田园诗,或者被寄托了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对亡国的遗憾与愤恨,或者是身世之感的附着。“田园”所指向的精神空间,在此时被充分地扩大了。在北朝,庾信长期处于不受信任和重用的地位,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官职和薪俸被迫躬耕。庾信能对陶渊明的田园诗有所继承,这大概与他在北朝的经历有关。而漂泊与穷愁交织的田园生活体验,也在唐代的时候为杜甫全面吸收。如《园庭诗》,反复感叹自己没有相交、相遇之人,只能孤独逡巡于园庭。诗歌中提到的物事,无不透露着萧瑟与凄凉:杖乡从物外,养学事闲郊。郊愁方汗简,无遇始观爻。谷寒已吹律,檐空更剪茆。樵隐恒同路,人禽或对巢。水蒲开晚结,风竹解寒苞。古槐时变火,枯枫乍落胶。倒屣迎悬榻,停琴听解嘲。香螺酌美酒,枯蚌藉兰殽。飞鱼时触钓,翳雉屡悬庖。但使相知厚,当能来结交。《归田诗》中,同样寄托庾信深刻的身世之感,虽然触目皆是在叙说田园中的生活片段,交代了自己闲适的村居状态,但实际上又意有所指。特别是这句“苦李无人摘,秋瓜不直钱”道尽了他初至北朝时受到的冷遇。而“社鸡新欲伏,原蚕始更眠”则是表明了自己甘愿蛰伏的决心。田园生活在这里不仅仅是对归隐的选择,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暂时让步。他甚至自比为张衡,在诗歌的结尾中说,“今日张平子,飜为人所怜。”在蛰伏北土期间,庾信展现了一种与陶渊明不同的隐士情怀。陶渊明在他的田园生活中,常常展现自己与乡邻把酒言欢、共食鸡黍的生活,并将这份农人生活的朴素的热闹,写在诗中寄给友人们。他的田园诗也因此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温暖,与甘愿浸心其中的满足感。下面可以来分析一些具体的诗歌。寒园即目诗
寒园星散居,摇落小村墟。游仙半壁画,隐士一床书。
子月泉心动,阳爻地气舒。雪花深数尺,冰床厚尺余。
苍鹰斜望雉,白鹭下看鱼。更想东都外,羣公别二疎。
庾信是特殊境遇下被迫归隐田园的。在寒冷的北国,他更有意表现出对田园生活之孤清的多层理解。他在诗中所塑造的个人形象,也是清冷、孤傲的文人隐士形象。结合冬天清冷的物候,来写隐者高尚的志节,是这首诗的特点。他强调自己住的地方,是一个寒冷的小园子,而且还很荒僻,在一个村墟在如星星散落分布。幽居值春诗
山人久陆沉,幽径忽春临。决渠移水碓,开园扫竹林。欹桥久半断,崩岸始邪侵。短歌吹细笛,低声泛古琴。钱刀不相及,耕种且须深。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
这首诗,是写春日里的隐居者,春日的和暖,让这首诗开头的气氛和柔。将自己形容为久已离开人群的“山人”,在自己有幽径的小园之中的路上,感受春天的忽然降临。这个季节,适合疏通园子里的水路,扫清竹林中去年沉积的落叶。园子里有一些破败的样子,桥已经半断,池岸的边沿也有些脱落侵蚀。但即便如此,并不妨碍在此中吹笛泛琴,拥有宁静岁月。诗的结尾,提到了钱。这在六朝诗中并不多见,可见当时穷愁的境遇,让庾信对此有所留心。孤身在北,他担忧的正是生计问题。于是他最后用了汉赋的典故慨叹,自己也想像写司马相如为汉武帝的陈皇后所作的《长门赋》,但是,该到哪里去求这卖赋而得之黄金呢。庾信甚至也会以“穷愁”为题,来写当时的生计。这类诗中,庾信将自己写成了贫士,也会使用陶渊明诗中的那些经典意象,比如菊花和酒,以及无无弦琴。卧疾穷愁诗
危虑风霜积,穷愁岁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屡惊心。
稚川求药录,君平问卜林。野老时相访,山僧或见寻。
有菊翻无酒,无弦则有琴。讵知长抱膝,独为梁父吟。
诗开篇的第一句,在风云岁月之变中,暗含了对政治时局剧变的真切感受。这种感受,不仅仅是岁月流逝、穷愁潦倒,而更是诸般的焦虑和恐怖感。以至于有一些杯弓蛇影的痛心、惊惧。为了应对这些惊惧,处于疾病之间时,也曾求药,也曾占卜。于是踏步平林,寻访野老山僧,以求解救。但肯定是无果的。学陶渊明,但是比他还要穷困,园中即便有菊花,罇中也是无酒的,无弦琴倒是有,但是它是无声的。在一切陷入无解之时,他慨叹自己的命运何以走到这样的一步——哪里知道在人生的此刻,只能独自久久抱膝,低吟一首《梁父吟》来安慰自己。《梁父吟》有写成《梁甫吟》,这是《梁甫吟》是三国诸葛亮(存疑)创作的一首乐府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诗中全是惊怖的景象:“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这样的诗,成为后世政治惧祸的代言,慨叹的是士之处世,何其如履薄冰,何其不易。在这样独居环境中,庾信的高超诗艺体现在他对田园生活细节的刻画上。如他的《山斋诗》中写到的田园景物:“圆珠坠晚菊,细火落空槐。”这里将露珠、萤火与植物们的交错之景,写得极为纤巧,气氛静谧悠远。而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所撰写的一些五言绝句,精致小巧,韵味悠长,为田园诗这一类型注入了隽永的艺术特点。如《春日离合诗》二首,之一曰:“秦青初变曲,未有逐琴心。明年花树下,月月来相寻。”之二曰:“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庾信在北朝生活的后期,逐渐摆脱受到冷遇的政治地位,开始和北朝贵族们有了一些唱和诗,互相赠酬。在这些场合诗中,庾信用精巧的笔墨描写了他所处之“园”,展现的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精致与优游。如《同颜大夫初晴诗》中所写的是“湿花飞未远,阴云敛向低”“香泉酌冷涧,小艇钓莲溪”,再如《答王司空饷酒诗》更见韵致,达到了文人化田园诗风神之最,诗歌头四句曰:“今日小园中,桃花数树红。开君一壸酒,细酌对春风。”此中似乎犹见当年身在南朝时候的富贵优游之态。庾信在田园诗中叙写的精神趣尚,与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小园赋》的主旨不谋而合,只是在赋作中,庾信对田园更是不吝铺排,可以视为他在北朝田园生活的一幅全景。它开篇以用典来名志,中间又以白描手法来写小园,同时还穿插对当年在梁时出入东宫的早年回忆,怀念故国,追忆岁月,可谓志深笔长。尤其是中间对田园生活的记述,已经脱却南朝咏物的精雕细刻之法,完全是对日常居隐生活的朴实记录。这是一篇非常值得详细解说的小赋。王绩、储光羲和李颀:人生取舍与被珍念的田园饮食除了春日和美酒,隋代诗人王绩常会在诗中写一些田园生活中非常慵懒的片刻。比如这篇:食后田家无所有,晚食遂为常。菜剪三秋绿,飧炊百日黄。胡麻山麨样,楚豆野麋方。始暴松皮脯,新添杜若浆。葛花消酒毒,萸蒂发羹香。鼓腹聊乘兴,宁知逢世昌。
这是一篇关于田园美食的诗,其中丰富的田园菜品,被写得让人馋涎欲滴。王绩情绪高昂地分享着他在田园间生活时所喜欢的蔬菜肉类。他开篇又是“无所有”这种套路,还加上一句说明:“每天饭都吃得晚”,然后开始列举那些好吃的:“菜剪三秋绿,飧炊百日黄”,这里应该说的是韭菜和韭黄。过去的人吃韭菜,用的是剪的方式,从菜园取出。所以杜甫也有“夜雨剪春韭”这样的描述。还喜欢吃“胡麻山麨样,楚豆野麋方”。他还提到了自己这顿晚饭喝的酒,是杜若泡的药酒,而且喝完了之后,他还吃了葛花,用以解酒。他的肉汤中,放了萸蒂,于是散发了更美的香味。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就鼓着肚子写了这首诗。储光羲创作田园诗,主要是在他隐居终南山之前的岁月。殷璠认为储光羲的诗歌语言,寄慨遥深,更接近孟浩然,说他是“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得浩然之气”。事实上,储光羲观察田园的视角,比王、孟要更为精细。储光羲以田父野老的心态去观察农村田园,因此他的田园诗开始细密地表现农事活动,写了许多射雉、采莲、耕种、收获、酿酒等农业事象,也写田园生活中的日常饮食,菰米菊酒、饭稻羹莼。从描写人物的方面来看,储光羲的田园诗也不再是泛泛而论,他写到了农业社会中的人物群像,描写了农父、渔父、樵父、牧童、采莲女等多种类型。这些都是农村田园生活里常见的人物形象,描写得很亲切、细致、自然。而写樵夫斫枝、渔夫垂钓,但内在似乎又有隐逸、得失的寓言之笔,抒发的是远离尘世、偏居世外的理想。这组诗,在盛唐山水田园诗中,无论是题材还是讲述田园的语言艺术方式,都是非常特别的。储光羲很注重从陶渊明诗歌中吸收描写经验。不过,他对田园的观察更为看重实物细节,钓鱼湾、榆柳、桑田等景物都会入诗,而一些具体的物事比如葵藿、禽雀、蟪蛄、蚯蚓等,也写得很生动。甚至他也会写到一些田园生活中的小事,如:吃茗粥作
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
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
数片远云度,曾不蔽炎晖。
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
敝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
这首诗写暑热之际,挽留客人喝粥,劝他日暮再还家。喝粥事小,却因为有着日常之中的人情滋味,而焕发了诗意。盛唐田园诗创作的代表,还有一人似乎是被遗忘的,那就是李颀。他是河南颍阳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新乡县尉,后辞官归隐到颍阳之东川别业。他在文学史中,主要是以边塞诗人的身份而著名。历代以来,很少有人提及他写过的田园诗,甚少进入明清时代的诗歌评点。但是,从他的生平和诗集来看,田园诗是他非常重要的一类作品,他在其中投入了很多深邃的人生思考,也因此而表达过自己对人生的诸多取舍。李颀将田园视为出仕的相反面,因此他的诗中,田园的相关内容,会被视为是一种隐居方式。比如《东京寄万楚》:濩落久无用,隐身甘采薇。仍闻薄宦者,还事田家衣。
颍水日夜流,故人相见稀。春山不可望,黄鸟东南飞。
濯足岂长往,一樽聊可依。了然潭上月,适我胸中机。
在昔同门友,如今出处非。优游白虎殿,偃息青琐闱。
且有荐君表,当看携手归。寄书不待面,兰茝空芳菲。
采薇,本是易代之际两位殷商臣子不愿食周粟而去采薇而食的气节故事,在这里的用典是取其有隐士风味的一面。而仕进上不顺遂的人,就会去重新穿上田家的短衣。这首诗所写给的对象万楚,是被李颀当作一位田园故人的。其中出现的春山黄鸟、樽酒潭月,似乎是他们依稀共同经历过的往事,又似乎是共同对他日还归田家生活的畅想。这是两个从田园故土往城市中求宦的年轻人,他们感受了命运沉浮,昔日同门之友,而今人生已经各有差别。虽然末句对万楚颇有鼓励,但前面所慨叹的“故人相见稀”和“春山不可望”,则已经让这首诗笼上一层挥之不去的轻愁。这种因为薄宦之旅而提及故乡和故人的风俗物事。如《寄万齐融》中的这些句子:“小邑常叹屈,故乡行可游。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为政日清净,何人同海鸥。摇巾北林夕,把菊东山秋。对酒池云满,向家湖水流。岸阴止鸣鹄,山色映潜虬。靡靡俗中理,萧萧川上幽。”这些对故乡田园的怀念,与对归隐之心的抒发,凝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含蓄有力的温厚情感。李颀的诗,也同样出现了田园与山水合流的情形。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田园节候中的习俗,会与对山水的张望,齐头并举于一首诗中。如: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
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
云入授衣假,风吹闲宇凉。主人尽欢意,林景昼微茫。
清切晚砧动,东西归鸟行。淹留怅为别,日醉秋云光。
重阳节候,菊花酒,茱萸汤饼,风吹云动,林景微茫,晚砧清切,归鸟飞来。这样的场景,如果说它是山水诗,那么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山水之奇崛的描述,如果说它是田园诗,似乎又没有农人樵夫的真切农耕场景。所以,这首诗,带有一种浓郁的融合气质,它是升华于田园的日常之上的一种精神表现。正如陶渊明在他的躬耕生活中,也会去写《九日闲居》,那种不问世事,但饮菊花酒的人生片刻休憩。李颀在他的行宦生涯中,对故乡田园还有一种心情,那就是焦虑它的荒芜、疏落。游子已经离开故乡太久,故乡的陇亩是不是已经荒草丛生?这种象征意象,在他的诗歌中非常常见。在他告慰那些人生仕进路上不太得意的人时,会常常提到一个这样的想象中的故乡,那是一个“寒园”或者“荒园”,似乎在告诉对方,人生还有其他的意义,比如去追回已经失去的“园”,让它从此不再寒与荒。如这首:送刘四
爱君少岐嶷,高视白云乡。九岁能属文,谒帝游明光。
奉诏赤墀下,拜为童子郎。尔来屡迁易,三度尉洛阳。
洛阳十二门,官寺郁相望。青槐罗四面,渌水贯中央。
听讼破秋毫,应物利干将。辞满如脱屣,立言无否臧。
岁暮风雪暗,秦中川路长。行人饮腊酒,立马带晨霜。
生事岂须问,故园寒草荒。从今署右职,莫笑在农桑。
大约是长期沉沦下僚,所以李颀对刘四的安慰,未尝不是一番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刘四是一个神童,9岁便能写文章,曾经何其有抱负。而且,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郎官,奉诏宫中,以至于有“童子郎”这样的美誉。但是,此后,就一直沦落在洛阳的县尉之类的底层小官职上。宦海沉浮,那些看似辉煌的过往、值得称颂的才能,纵使全部回忆一过,那就如何呢?一种真实的苍凉心情,放在了诗的后段,这些才是对刘四当下境遇的深刻同情,而这些话所对应的事实,李颀是没有去明说的。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内容,出于一种善良,不去揭破。刘四此去,是在一个岁暮的冰霜寒冷之日出发,去奔赴某个小小职位,他对命运是困惑的。但李颀安慰他说:“生事岂须问,故园寒草荒。从今署右职,莫笑在农桑。”类似这样以故园来安慰或者动情宦游者的诗,在李颀这里还有不少。《送裴腾》中的裴腾,也是一个“还令不得意,单马遂长驱”的宦游之人,而此时相送,李颀用以安慰他的物事,皆取自田园:“桑野蚕忙时,怜君久踟踌。新晴荷卷叶,孟夏雉将雏”,而诗的最后,同样留下念及故园荒芜之存想,仿佛是为裴腾规划出了一个永恒的灵魂归处:“香露团百草,紫梨分万株。归来授衣假,莫使故园芜”。《崔五宅送刘跂入京》也是一首类似章法的诗,诗云:行人惜寸景,系马暂留欢。昨日辞小沛,何时到长安。
乡中饮酒礼,客里行路难。清洛云鸿度,故关风日寒。
维将道可乐,不念身无官。生事东山远,田园芳岁阑。
东归余谢病,西去子加餐。宋伯非徒尔,明时正可干。
躬耕守贫贱,失计在林端。宿昔奉颜色,惭无双玉盘。
“乡中”与“客里”,是李颀诗中被对立起来的两个空间。而“客里”即意味着长期的行路。行路之间,只能见到孤鸿,感受风日之寒。于是就分外四年故园:“生事东山远,田园芳岁阑。”这里的“东山”,也即为官,是为王事而奔波。这种奔波到头其实并不如“躬耕守贫贱”这样的抉择。当然,李颀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躬耕守贫贱”,作为地主阶级,他拥有自己的别业,他的朋友们,也有别业。这些以故园作为劝慰之言的送别诗,其实是他们的山水庄园罢了。比如,李颀自己也有一座“东川别业”,他曾经写过一首《不调归东川别业》,诗题如果是他自己所立,那么意思很明显,意思是官运不通,故而归于自己的别业庄园。他懊悔自己长期游宦,而与这座别业缺少亲近。在写到别业中的田园风光时,他的用句也很古朴可爱:“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十室对河岸,渔樵祗在兹。青郊香杜若,白水映茅茨。昼景彻云树,夕阴澄古逵。渚花独开晚,田鹤静飞迟”。他所写的“东园”,应该也是指这座别业。如《晚归东园》形容了此间的风景:“出郭喜见山,东行亦未远。夕阳带归路,霭霭秋稼晚。樵者乘霁归,野夫及星饭。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这是一幅非常温馨的晚归图。再比如,李颀在诗中详细写过朋友们的别业。如这首:裴尹东溪别业
公才廊庙器,官亚河南守。别墅临都门,惊湍激前后。
旧交与群从,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长啸对高柳。
清欢信可尚,散吏亦何有。岸雪清城阴,水光远林首。
闲观野人筏,或饮川上酒。幽云澹徘徊,白鹭飞左右。
庭竹垂卧内,村烟隔南阜。始知物外情,簪绂同刍狗。
这位在河南做太守的朋友,有一处东溪别业。每十天工作日之后的假期,就有旧朋新友一起携手在其中玩耍。所有人非常沉醉于这种“散吏”的状态,享受这种人间的“清欢”。他们在这个庄园之中,田园风光只是他们观看的对象:“闲观野人筏”“村烟隔南阜”,这些都是他们端着酒杯在旁观和欣赏的而已。李颀也写过一首关于老农的诗,同样是以旁观的态度,来羡慕他所拥有的田园生活,并非是一首悯农诗:野老曝背
百岁老翁不种田,惟知曝背乐残年。
有时扪虱独搔首,目送归鸿篱下眠。
这种闲逸,才是李颀对田园的真正的眷恋之处。以上所谈,拉杂散乱。但是,在时代变迁之中,家族或者个人的漂泊流寓引发的乡愁中,田园饮食所承载的情感记忆,是非常强烈的。在人生的进退取舍中,故园饮食也会成为被取舍的一个部分。在先秦以来的农事诗从文人诗中逐渐消失之后,饮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写进文学作品,而西晋束皙所著《饼赋》曾被视为俗赋,并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在此后中古文学作品中,乡愁对田园饮食的书写,做了一种情感的提纯,让这些物事在失而复得的田园归趣,或者是在长久忆念的田园思念中,变得富含诗意,甚至升华为一种纯粹的人生哲学的象征。注释:
[1]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绪论”,齐鲁书社,年,第1-页。
“汲古论坛”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取意赵朴初先生“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题词。旨在研讨古典文史哲艺相关问题,转载请注明:http://www.js-zodiac.com/jhxg/117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