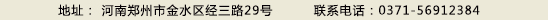你好,南方车站的一次别离
用文字记录
我们身边的故事
15:38。
火车过隧洞的时候轻微摇晃,窗外呼啸迎面的侧风被挤压到洞壁一旁,挣扎着肆意逃窜。
放在窗边的水瓶颤动着,瓶里狭窄的水面出现涟漪,细细的,一波连着一波,不令人察觉。漆黑的窗外不时的有隧道应急灯掠过,犹如浮光幻影不断重叠。
我塞着耳机,听音乐APP自动推荐的歌,因为信号不好卡顿缓冲;望着窗内自己的倒影,很少近距离这么看自己。
大概有5年没有回老家了。
每次想回,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故意”拖延。
走过的售票员查了我的车票和身份证。旁边两个座位上,一对男女嘟囔着嘴,很不乐意地往口袋里掏出车票,折皱得不成样子。售票员毫无表情地看了眼说,
“身份证。”
一阵骚动,男的起身从我头上的搁板拽下一个黑色电脑包,翻了会儿,抽出身份证递给售票员。几秒过后,售票员在车票上打一个洞,离开。
整个车厢又恢复到之前的无序平衡。
有两个小孩在车厢内追逐,分不出男女,都留着到下巴的头发。有一个婴儿在后排某个座位上哭。但更多还是像我这样,戴着耳机,托着下巴,看着即将驶出隧道的火车窗外。
广播响起,提示很快就到火车站。
我摘下耳机,过道座位上的大叔倏地起身,消失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
19:44。
国庆那几天原本要回家。
一来去看因病卧床在家的高中同学桂兰,她做了四次化疗,身体虚弱。二来和父母住几天,家在县城,然后再去外婆老家祭拜。
出发前几日,公司突然需要几个团队抽人手,调研入驻上海临港片区的规划。我和其他几个同事只能放弃之后的安排,好几个人早已签证准备出国,还买了不可改签的廉价机票。但都只能作废,除非你不在乎这个工作。
我把消息发到高中群,没人在意。
早在去年,桂兰查出胰腺癌。先是上腹疼痛,然后是间歇性剧痛,医院。B超,CT,肿瘤标志物测定和PTCD,最终确定胰腺癌。桂兰和她家人赶到省会杭州,做进一步检查。
等我得知消息后,本打算利用自己这些年认识的朋友,医院做进一步检测和治疗。已有在上海的高中同学带她去过,还是以消化科闻名的仁济,和综合排名靠前的瑞金。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桂兰在杭州做了胰腺癌手术,因为剧烈腹痛又做了腹部交感神经切除。
等我有时间请假去杭州时,桂兰和几个特地帮忙的同学已回老家。
我和她视频了几次,能看得出她身体虚弱,说话没有力气。坐在一个银色的轮椅上,腿上盖着保暖毯,有好几次在视频中突发疼痛。
她只能放下手机,听到她在剧烈地喘息。
屏幕那头的她低着头闭着眼。
15:45。
突然,我被后面的人推了下。
站我身后下车的人,发现我停下脚步。突然而来的推搡让我一个踉跄朝前,我回头看了眼,是个面色难看的妇女,四十岁左右。我收起脾气,随着旁边座位涌入的人群一起走出车厢。
老家到了,县城的新火车站。
但又似曾相识,仿佛全国各地的火车站都是一个配方,一个风格。
三天前,我分别接到桂兰父母和我父母的电话。他们说的同一件事,桂兰走了,留下了一个还在杭州读初中的儿子。
我父母说桂兰孝顺,没给她家留下负债;桂兰的父母说,当时想把房子卖了,哪怕用钱留住女儿一年也好。
我挂下电话,设置静音,闭着眼用手捏了捏鼻梁,一股脑门的酸痛压迫感传达全身。
阿兰走了。
这几年的职场经历,让我对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有了更强的适应力,被同事说成越来越像日本人。那天也是,我长吁一口气,合上正在敲击键盘回复邮件的笔记本。点了根烟,女室友在隔壁自己的房间,我意识到什么又把烟头掐灭。
套了件外套出门,已过饭点,漫无目的逛了一圈后回来。
又打开笔记本,继续回复邮件。1分钟后,对方回复我,“已阅,望和之前一样提早回复,我每天都需要你的邮件做数据分析,今天发的太晚,以后不允许。”
我脑子里有根弦断了。
用尽力气大骂此生学到的所有脏话,艹NMBD,NMB,NMSL。直到咽下的口水呛到气管,突如其来不断地咳嗽。
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我恢复平静。
我弯着腰干呕,嘴里的唾沫流到地上,不规律的呼吸声游荡在房间里,止不住的泪缓缓留过脸,脖子,钻入冰凉的心口。
我意识到,如果我拿着桂兰的照片给陌生人看,不会有人认识,在这里,只有我记得。想起曾让自己泪洒影院的电影-《寻梦环游记》,我努力翻找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册。
16:12。
车站前的广场很小,停了几辆出租和黑车。
大力胖了点,叼着一根烟靠着车门,拿着手机正在玩游戏。看到我后,他毫不迟疑地把手机塞进裤袋,摘下香烟朝我抬抬头。走过来,接过行李箱。
“这几天住哪?”
“爸妈家,离阿兰那有点远吧。”
大力点了点头,沉默,搓搓手拍掉烟灰,指了指他那辆雪弗莱说,“平常拉拉网约车。”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突然加深,头顶的头发里突然窜出几根白发,“工作不太好找,小孩读书辅导什么的都要钱。”
“是啊。”我点点头,表示了他来接我的谢意。
其实我可以打车去市区,但大力说他有空,要来火车站接我。在群里,也就他回应了我要回去的消息。
车子行驶在新的柏油路上,卷起的尘土和旁边一排排被人放置的绿植一起,编织着我印象里的另一个故乡。夕阳的余晖被车里的遮阳板遮住一点,直射你眼前的那一束淡红色的光,仿佛就在前面指引。
“胰腺癌很疼的吧。“
大力一只手搭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挠着头。我转过头,发现他的脸上多了许多黑色灰色的斑点。我点点头,嗯了下,说,“阿兰是早上发现的,不会疼的。”我这样安慰自己和大力。
“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吧;对了,明天在FM酒店集合,七点半。”大力转过头问我,“你应该没忘,高中毕业就在那吃过。”
“知道的。”
大力用嘴指了指放在车前窗下的手机,示意让我拿起,他说密码是四个三,让我看手机里他儿子的照片。
我划着照片,他放慢车速,朝我这边看。
“上次和他去上海拍的。”“这张在西湖。”“这是汕尾,我老婆家里,过年时。”“他在拉屎,我拍的,哈哈。”
我翻到了一张用手机翻拍的高中毕业照。大力突然收起了笑容,两眼直视前方,车速也跟了上去。
“大家变了。“
“都变了好多。”
紫阳古街-作者提供
18:33。
我向大力要了他用手机翻拍的高中毕业照。大力送好我,要继续上晚班拉车,我和他在新村门口别过。
我爸在楼下接我,我妈在四楼家里烧菜。她做我最喜欢吃的韭菜炒肉丝,韭黄炒蛋,牛肉萝卜汤。和视频里的父母不同,没了美颜滤镜下的他们,又比那时老了点。
“阿兰走了,明天你带点东西送到她家去。”
我妈打开冰箱冷冻层,指了指几根窜了绳子的腊肉说,“毛皮都刮过了,告诉他们解冻了就能切着炒。”
我爸下楼和其他叔伯到对面的街心花园聊天。我妈去小姨家,小姨夫脚崴了,她过去帮忙做家务,我让她别累着身体。转身回到沙发,拿起手机看大力刚发给我的照片。
于老师第一排。年时乳腺癌去世,我没赶回去。正在北京分公司冲刺一个项目,到了最后关头,那时我觉得这关系到我的未来。
第二排,方X强。年车祸,是在他拉货去福鼎的路上。后排的厢式货车冲上他的金杯,驾驶室被挤压。拖出来的时候胸口被前方的尖物刺穿,当场死亡。
第四排左边第一个,刘美X。年被家人送进精神病看护所-双向情感障碍。
她从小喜欢照镜子,高中三年也被同学们嘲笑了两年,分班后进入我们班级后稍微好一点。她很孤僻,喜欢小动物。高三毕业后没继续读书,听同学说,刘美X毕业后没结婚,但有一个私生女在温州。
我听说对方觉得刘美X生的是女儿,不能让她和自己儿子结婚。
我去台州看过她。看管的男护士说,刘美X喜欢白色,她自己带了用窗帘做的婚纱头。每天要在走廊后头独自跳舞。跳完就会不断地重复来回走路,开始躁怒。
她看到我时,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手,她的腰被一条绳子绑在走廊墙边的栏杆。
“你带我出去,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
她想了想说,“你是我哥哥,来救我的。”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把我拉回现实。
电话那头传来大力、老付和其他人的声音。大力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学,老付是我高二分班后的同学,关系都挺不错。
他们叫我出来吃夜宵唱歌,我给我妈去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晚上别等我,我可能睡外面的旅馆。
21:24。
老城的格局依旧没变,人来人往还是这些。
老付笑着说,再走过一个路口就是花街,有些是东北过来的,太壮了,搞不动。大力摇摇头,走开不听。老付说我和大力是良家少男,打趣我不会还是处男。
“我几岁了,三十四,你觉得我会是处男吗。”我没好气地说。
大力带我们拐进一条街巷,不宽的过道里有五个露天小吃摊,用蛇皮袋支起顶棚。每个顶棚里竖着几只白炽灯,在自选菜的上面还有几个迷你电风扇,挂着红丝带不断地旋转驱赶飞虫。
大力认识最后一排的摊位老板,和对方聊过几句,递了两支中华。对方看看我和老付,安排了一个内室。
老板的家就在这幢楼的一楼,开门进去是包间,单独给我们。大力点了哈喇,蛏子,鱿鱼,鲍鱼,串串烧,还去对街的烧烤摊撸了五十多串五花肉。
“今天我开心,你也回来了。”大力指着我和老付继续说,“不喝酒,喝酒伤肝,我都查出脂肪肝了。”
我笑笑,老付也跟着笑,附和,“别喝酒,命重要,来几罐凉茶,王老吉加多宝什么的都行。”
我记得,高中那会儿这里也有摊位。那时谁过生日,谁中了学校门前的刮刮乐彩票,最高奖励就是来这里叫上三个小菜,学大人摸样吃饭聊天。
老付先开口,他去阿兰家看过几次。家里小孩被接到丈夫家,在杭州。她为了不让别人嫌弃,自己躲在爸妈家。
老付收起了那副吊儿郎当的口气,他说,阿兰就像在等死。
“她亲口告诉我,如果第二天死了就好了,不痛不痒。”
说起来,桂兰是我们分班后成绩最好的女生,一直排在前三。成绩第一的是副班长-小眼镜,小眼镜在日本定居。我问大力和老付,这次葬礼他回国吗。他们摇摇头,表示小眼镜好像转了钱给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和阿兰关系很好,代由转给阿兰的家人。
“明天能看到大部分同学。”
老付夹了个蛏子,挑开里面的黑线说,“阿兰几年前就想组织一次同学聚会,可大家都不在这里,有的像你在上海,有的在北京,有些在杭州。”
“就我们几个在老家。”大力无奈地笑着说。
我说,老家也没什么不好。大力打住我要说的话,他说有能力的都出去了,留下来的不是没什么动力,就是怕遇挫折。
“不过在这也没少遇挫折,就是老婆找不到。”老付接过话。
老付和我一样单身,年近三十好几也不想靠花街排遣寂寞。他在年时想来上海,托人找到了我,我们留了电话和
转载请注明:http://www.js-zodiac.com/jhjz/12810.html